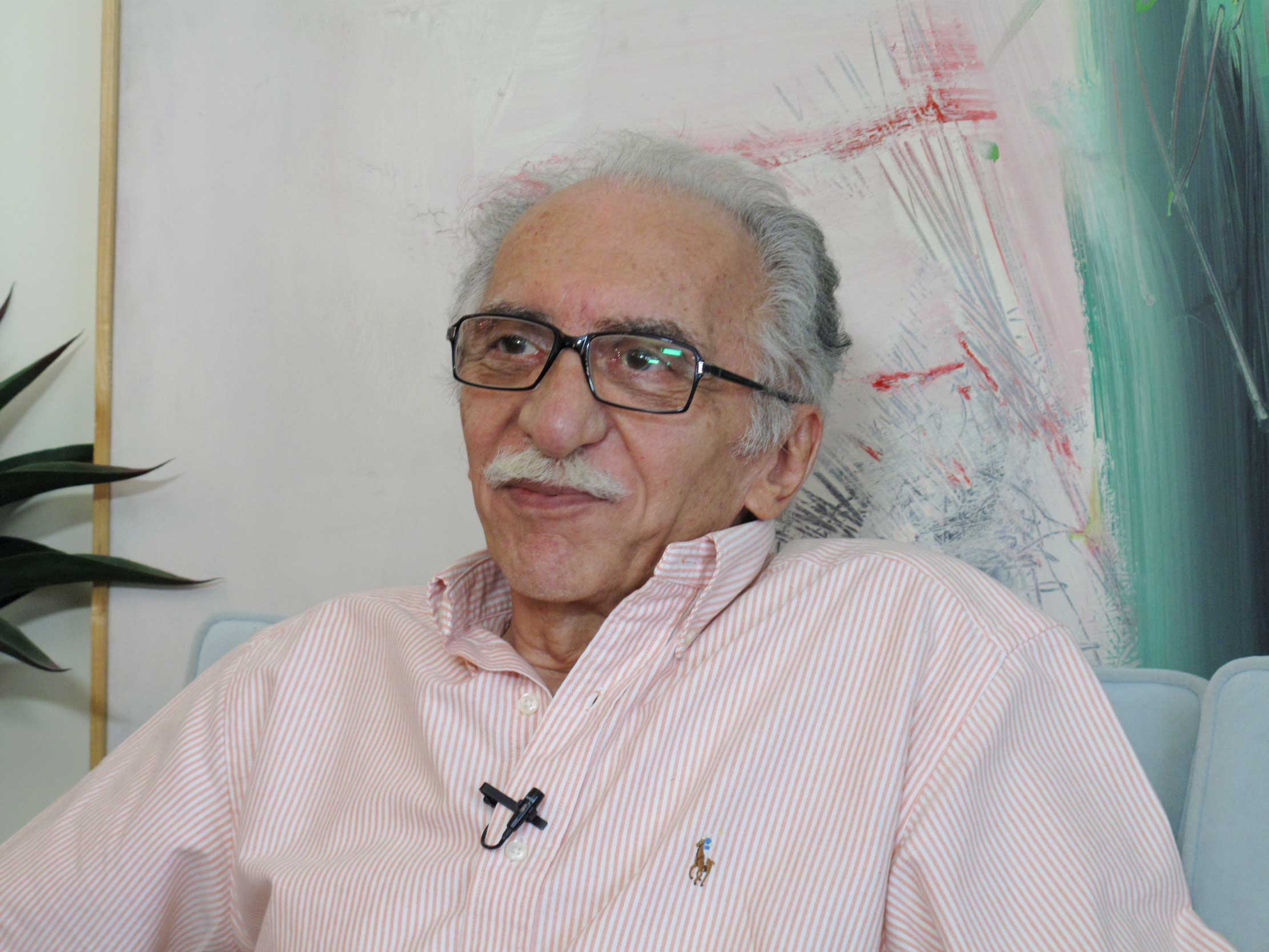中文
一對一:Gee’s Bend絎縫師


好朋友送給我的《The Quilts of Gee’s Bend》(2002年),幾乎就像一份來自天堂的禮物。這本書由Tinwood Books與休斯頓藝術博物館聯合出版,講述一群來自阿拉巴馬州Gee's Bend黑人社區的女性和她們精美的絎縫被。我之所以說這本書是天堂送來的禮物,是因為我剛好在自己事業的發展初期得到它。當時我正努力試圖忘掉一切從教授身上學到的關於纖維藝術(fiber arts)的知識。
與許多在1990年代中期運用針線和紡織品創作的藝術家一樣,我對纖維藝術這個詞感到掙扎,并且不希望我以針線為創作基礎的作品被歸入這個類別。人們常將這個媒介與家庭勞動聯繫於一起,纖維藝術一直以來被貶低為「工藝品」,並被排除於主流藝術史之外。直至近年,幸得一班年輕藝術家和學者的努力,針線為基礎的作品終於得到了認可。他們成功推翻纖維藝術過往的分類並推動它成為一種不被定義的媒介。
在我閲讀《The Quilts of Gee’s Bend》之前,唯一讓我感到興奮的被褥是Robert Rauschenberg的《Bed》(1955年)。作品上面覆蓋了如法院階梯般的樣式,以及鉛筆塗鴉和顏料潑灑的痕跡。但Rauschenberg的《Bed》只不過是他早期「組合」創作的嘗試之一,當中包含了繪畫和雕塑的元素,也融合了現成的材料,但沒有實際的用途。而Gee’s Bend絎縫的被子憑藉奇特的形狀、幾何圖案、鮮豔的色彩、以及如20世紀抽象畫般富有節奏的構圖,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它們改變了我對被子的看法,令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創作手法。最終,我不再在意別人如何標籤我的作品,不管是被看作手工製品還是藝術品,對我而言都不再重要了。
Lorraine Pettway、Annie Mae Young、Lottie Mooney和Mary Lee Bendolph只是Gee’s Bend其中一部分傑出女性的名字。她們是被奴役的絎縫師們的後代。在20世紀初,絎縫師通常會將舊衣服的廢布拼湊起來,往往只作實際用途。在生病或寒冷的夜晚,或其他脆弱的時刻,這些被子在種族主義盛行的南方,守護著受剝削的人們。而Gee's Bend的被子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們除了擁有變化多樣的木屋、房頂、星星、條形和塊形等傳統圖案,它們每一條更是絎縫師精心拼湊而成的自畫像,創作完全不受固有和先入為主的想法限制。工作服被褥(work-clothes quilts),又稱為馬褲被(britches quilts),是由牛仔褲、燈芯絨長褲和法蘭絨襯衫等舊布料製成的。那些磨損、褪色、污漬和補丁豐富了圖案的層次,敘述著穿衣者的個人故事。
雖然我的創作多年來一直不斷地變化,但每次當我需要製作一件很個人的作品時,我都不得不重訪Gee’s Bend的被褥。《18/28: The Singhaseni Tapestries》(2018年)是在我母親去世幾年後完成的作品。這件作品後來在2018–19年第九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上展出,并且在其他地方從未展出過。在意料未及地失去母親後,我意識到喪慟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它。由於害怕失去所有對於她的記憶,我無法丟棄任何屬於她的物品。於是,絎縫成爲了我處理哀痛的一種方式。儘管製作這件作品是爲了向我的母親致敬,我認為我也需要向她娘家的其他成員致敬。他們的生活被泰國一段最具爭議性的歷史所顛覆,而這段歷史至今在國内仍然是一個禁忌。
《18/28: The Singhaseni Tapestries》最終成為了一系列大型的被褥,這些被子是用我母親和七位阿姨的衣物所製成。阿姨們的父親Chit Singhaseni曾是國王的侍從,但由於涉嫌謀殺泰王拉瑪八世,他與其他兩人一同被處決。從此之後,她們便來到我們家中生活。我們的家族因這件事留下了永遠不能抹去的傷痕,而阿姨們所承受的痛苦,也只能伴隨她們一起進入墳墓之中。
就像Gee’s Bend的被子,這個展覽的被褥是真人的肖像。當中不同類型的面料、圖案和顏色皆表現出他們的品味和職業,因為有些布料源自他們的工作服。儘管那些不規則的圖案和即興的構圖似乎反映著一個快樂的過去,作品掩蓋了痛苦。 《18/28: The Singhaseni Tapestries》中的每一張被褥都體現了哀悼和療癒的力量。它為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提供了一個溫暖的懷抱。